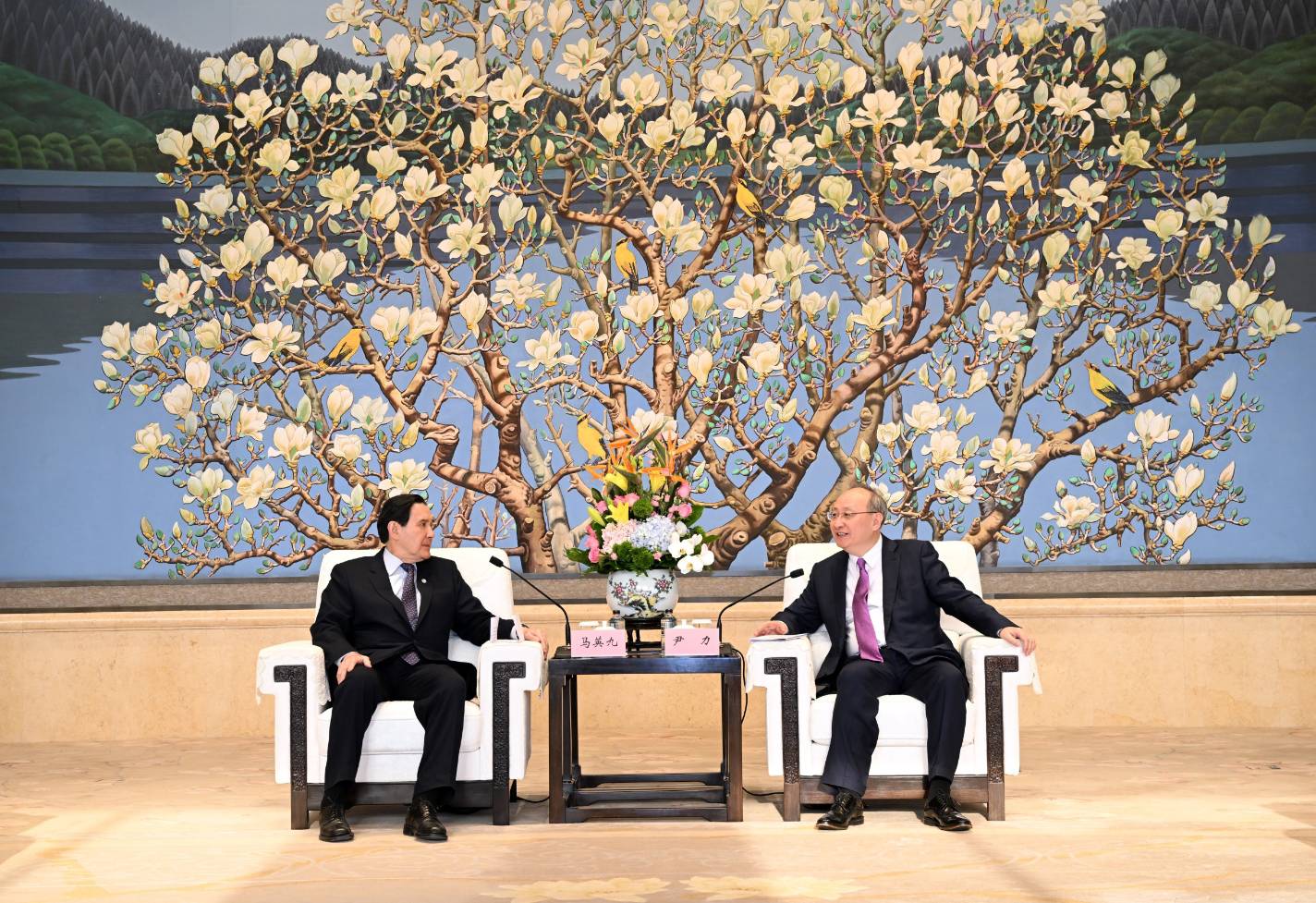编按:凋零不可逆,抢救不容缓,两岸故事在时间的字句中飞奔。沈春池文教基金会「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」计画,期能为大时代的悲欢离合留存历史见证,珍藏可歌可泣的「我家的两岸故事」。
网路上,有一署名林野撰写的「台北食事」,许多网友浏览后觉得嘴馋不已,还有人说,看得他直生津。作者林野自承来自香港,「开宗明义」谈的是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前五0、六0年代的台北食事,掐指算算,作者年纪应该与我相仿佛,但他对台北美食的记忆,似乎与我的记忆有些出入。
随便聊聊,切勿当真。毕竟,每个人的味蕾偏好和记忆,大不相同,不能一概而论。有些味蕾的记忆,也很可能来自于父执辈或其他饕客的转述,不是吗?狗尾续貂,算是补遗拾阙,不全之处,还待有心人接力完工。
「食事」的开场,将场景设定在五、六0年代,提到「信义路从安东街口到东门都是违章建筑,在那里可以买到包子、馒头、葱油饼之类的北方面食」,接着,跳转到「觅食族」学生到龙泉街吃大碗牛肉面,又跳转到中正桥头永和顶溪那儿的豆浆店。五0年代的台北,除非拥有自用交通工具,个人的横向移动能力极为有限,能够悠游于东门、师大附近和永和中正桥头者,亲尝各类面食美点,实属少见。因此,上述有关台北食事的的描述,不知是否根据作者的亲尝经验写成的?
民国五十四年,小五升小六的秋天,我从长春国校转学到东门国校。每天上学得到通化街临江市场搭三十路公车,从尚未拓宽的信义路,经国际学舍(也就是今天的大安森林公园)对面的小美冰淇淋和好几间狗园、穿过尚未填平的公圳上的水泥桥、经新生南路、东门、转仁爱路后,在仁爱路和林森南路口的泰北中学那一站(或是东门国校站)下车,再穿越十字路口到东门国校上学。
也许年幼,也许是那时公车少,班班客满,人挤人,瞧不见车外的风景;搭车上东门十个月期间,我几乎不记得安东街到东门的违章建筑有卖各式北方面食的摊商。
那时,初中联考犹在,恶补风行,东门国校又是个出了名的升学国校,六年级下课后,同学都得到级任导师家恶补数学。补习结束后,约莫晚上八点左右,三十路公车,晚间班次少,同学们习惯结伴步行到东门市场搭车,印象中,东门市场附近,也没甚么北方面食馆。反倒是东门国校斜对面、林森南路上各色南北小吃特多。
当时家里环境不甚富裕,晚间餐费拮据得很,只能在林森南路、泰北中学门口的违建摊商那儿买个五毛钱的葱花厚烧饼,随便啃啃,充充饥。偶尔调皮,跟着同学跑去卖烤鱿鱼、烤香肠的小车,打弹珠台,和老板比弹珠进洞点数大小,赢了,便可换张碾成网状的烤鱿鱼,解解馋。
以前,泰北中学的大门,和今天台北青少年发展处一旁的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别院钟楼,紧贴在一块儿。看似残破不堪的钟楼,小吃摊和饭馆林立。有一回,应该是模拟考考了个全校第一,奖励自个儿,补习前吃晚餐,破例选了一家面馆里,吃了一碗大卤面,那是我念东门国校时、唯一一次走进面馆吃面,也是生平的第一碗大卤面。
林野聊到水饺时提及,「刚来台湾时对饺子很感兴趣,因为出生在香港从未看过,记得火车站前方今新光三越)的空地有几家铁棚搭建的水饺店。」这段食事记忆,不知确实的时间点是何时?
民国五八年到六一年,我念高中时,台北车站是星期假日约女生郊游的集合热点(那时可没有这名词儿)。北车周遭和对面,小吃店和冰果店特多,独独不记得有水饺店的踪影。也许早期咱们邀女生出游,通常也会自备野餐吧?因此,不会特别注意有无水饺店。民国六十五年,我大学毕业,新光三越那块地儿,紧贴著南阳街补习班,确有一排以补习班学生为目标客层的小吃店。我没在补习班待过,不知该处有无水饺店。
作者的水饺记忆,到了龙门客栈,戛然而止。记忆无误的话,直到九0年代,龙门客栈应该只是台大法学院和医学院师生的共同记忆,外人知晓的,不多。反倒是日式酒吧林立的林森北路,南北小吃很多。
民国七0年代,3%的戒严令,仍在实施。南京东路林森北路口的极乐殡仪馆,尚未拆除,沿着林森北路上西侧,尽是各类小吃店,也是少数可以晚间吃个宵夜的所在。其中,夜猫族最爱的,要数禚家小馆(还是禚家水饺?)。禚家小馆的水饺、卤菜、快炒,都小有名气。报社下了班,开车冲到禚家小馆,来盘水饺,切盘卤菜,再来杯啤酒,人生一乐也,至于爱车,就丢给一旁代客停车兼洗车的小弟呗!
谈到水饺,我个人最怀念的,要算仁爱路巷子里刘家小馆的黄鱼水饺。我弃媒从商后,常常带上外国客户到刘家小馆尝鲜。吃过刘家小馆黄鱼和牛肉水饺的老外,曾对我说,北京的水饺没法比。当然,老外朋友说这话时,大陆改革开放的号角才吹响不久,北京水饺可真没法跟台北比。遗憾的是,刘家小馆已在几年前歇业了!
刘家小馆的黄鱼水饺有名,喜来登饭店还叫来来饭店时,十七楼俱乐部的黄鱼面,堪称一绝。如今,黄鱼面也成梦里记忆。
提到黄鱼,打个岔。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曾经带我们在台北吃过干煎小黄鱼和面拓黄鱼,上大学后,这两道佳肴似乎在台湾绝迹了!两岸开放交流后,九六年初履上海,居然吃到了久违的干煎小黄鱼。在那之后,只要到了上海,干煎小黄鱼便是我必点的美食。
从水饺记忆,林野老哥的味蕾转换到「鼎泰丰」和华山市场的「阜杭豆浆」。其实,鼎泰丰成名甚晚,算不上咱们这一代早期的食事记忆。高中时,还没有康青龙这个词儿,但永康街、青田街到龙泉街,可是咱们同学拎着篮球,招摇过市的势力范围。那时,永康公园旁,有名的是那家卖油豆腐细粉的小店,没听说鼎泰丰的旗号。鼎泰丰一旁的南京板鸭,倒是名店。如今,南京板鸭好像不见了,卖油豆腐细粉的小店虽然还开着,却难与世界名店的鼎泰丰,相提并论了。
阜杭豆浆亦然。之前,永和及四海烧饼油条豆浆,还在阜杭之上。永和、四海之前,好吃的烧饼油条豆浆,遍布台北,难分轩轾。我念大学时,父亲朋友请客,因缘际会去了当时卖烧饼油条豆浆最高档次的店儿吃早餐,那家店,唤作欣欣餐厅,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(从前都简称辅导会)下属的荣民供销中心开办的,既是蒋经国宴客的指定餐厅,也是小蒋吃早餐的场所。阜杭豆浆?抱歉!还真没听过。
如今因阜杭豆浆爆红、重新赢得消费者青睐的厚烧饼,以前多烤成菱形状,烧饼上头的芝麻特多、特香。我吃过最好吃的厚烧饼油条,是服预官役、担任三民主义巡回教官时,在澎湖马公的传统菜市场里吃的,至今回想起来,依然齿颊留香。味觉记忆能够持续至今,你道好吃不好吃?四十年青春梦回,不知那家烧饼油条「健在」否?
林野的牛肉面记忆似乎特别庞杂。郑州街、铁路医院、开封街、汉口街(正确地说,应该是延平南路吧)、龙泉街、清真、红烧,甚至二00五年台北牛肉面节,都在他扫描范围。不过,作者未及细数各家牛肉面的精妙处,只是特别描述了一下永康公园口上那家牛肉面摊。他说,「同一时期,一位退伍老兵在永康公园附近摆摊,不久创出了口味」。不知同一时期是指那个时期?
永康公园边上那家牛肉面摊,确实红极一时。搭着帐篷的小小面摊,常常「万头钻动」,入夜不久,人去摊空。原来,那老板很早就懂得饥饿行销的道理,每天牛肉面是限量的,卖完收摊。不过,从前、从前,牛肉面绝非平民美食,像我这种家道中落的「芋头番薯」子弟,只能点个牛肉汤面,尝尝别人吃肉我喝汤的滋味。
永康公园那牛肉面摊,直到我出了社会,自个儿会赚钱了,才有机会品尝。也不知是不是长大后,嘴刁了,说实话,那汤头、那牛肉,比起我自个儿烹煮的,差远了!
其实,永康商圈那儿,好吃的牛肉面店,挺多的。金华国小旁的永康牛肉面,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家的半筋半肉、粉蒸肥肠、粉蒸排骨和几道小菜,都很能征服老饕的胃。丽水街、淡江大学城区部旁的川味老张牛肉面,也挺够味儿。但印象中,民国七五年前,川味张牛肉面似乎不在这地点。
永康公园口的牛肉面摊,后来因市府整建永康公园和周边的巷道,给拆了!一旁的巷道口,后来就冒出了一堆冰店和面馆。往巷子里再走进一点,便是当年涉及江南案诸位「嫌犯」,商议大计所在的情报局招待所。《商业周刊》草创时期,那栋楼便是商周的办公室兼编辑部。
再往巷子里头走,横的那条巷,七0年代、八0年代,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的秀兰小馆,就在那儿。林野老哥写到隆记菜饭歇业,却没提到秀兰小馆,可见,咱俩的台北食事记忆,时序上,还真有些差距。我下海从商后,秀兰小馆在西华饭店对面开了家分店,国外客户来台若是下榻西华,我便会就近带他们去那儿大快朵颐。九0年代末期吧?秀兰小馆还曾挥师北上,进军上海古北口的洛城广场。上海朋友戏称那是「台湾口味的上海菜」,不多久,收了摊。如今,就连洛城广场都已拆毁改建,世事沧桑,不胜唏嘘。
谈到港式饮茶,林野的记忆聚焦在一九五八年创业、开在西门町那儿的马来亚粤菜餐厅。作者没提他自个儿在马来亚餐厅的「亲尝体验」,不过,知道马来亚餐厅的人,论年龄,今年至少也有六十五岁了!六十五岁的粤菜饕客,却没提早年衡阳路上的掬水轩餐厅,让我有点纳闷(也许作者移民来台时掬水轩已经谢幕了!?)。不仅如此,还漏了稍晚也在衡阳路上创立的大三元饮茶(非今日大三元。原大三元后迁至信义路安
和路口,改名静园,现已歇业),也颇不解。至于古早时赫赫有名的红宝石餐厅,提都没提,更是遗珠之憾。
马来亚餐厅的马来糕、叉烧包,都好吃极了 他们家的中秋月饼,更是当时台北、或者说整个台湾广式月饼的状元。不过,我们小孩只爱他家的枣泥、豆沙蛋黄和莲蓉月饼,对火腿、伍仁之类的月饼,则敬谢不敏。
作者怀念的「外省挂」美食餐厅,有二0一八年因都更歇业的「隆记菜饭」,五、六十年代大大有名、早已歇业的「三六九」(苏杭点心)和「陶然饭店」(潮州菜),沅陵街的「新陶芳」(客家菜),延平南路的「山西晋记」(猫耳面、涮羊肉),以及复兴桥下的「天桥饭店」(客家菜)。
或许这是作者「台北食事」系列的第一篇吧!?因此,没来得及将记忆库里missing link的挖掘干净 其实,台北美食餐厅巨多,谁能记得清楚?且容许我根据我的记忆库,补缀三家消失的一。它们是:
中华商场的「真北平」。真北平的招牌,中文之外还附着满文(?),跑堂穿着白色的袍子,食客进门,跑堂此起彼落地「高唱」著京片子,招呼客人。这样的排场,在台湾已成绝响。有机会到北京,还能瞧见。
还有,中山堂对面的「山西餐厅」。早期,山西餐厅是老国代、老立委和大官们应酬要地,他家的铜炉火锅和鸡油豌豆,是我最爱。山西餐厅后来搬到林森南路、来来饭店后门巷口,菜色和伙计招呼客人的「味道」,大不如前,在我心目中,此山西餐厅,非彼山西餐厅。
最末为汉口街、重庆南路口上的「复兴园」。我第一次光顾复兴园时,它位在敦化南路、土地改革馆附近,忘了何时搬到了开封街。复兴园应该是今天许多上海老餐厅的鼻祖。
正因为阿唐师父的复兴园,开枝散叶,所以,上海菜始终能在台北老饕圈中,拥有一席之地。复兴园退隐,或许也出自同样的原因吧!
味蕾不同、味蕾记忆也不同。在米其林星星没有引进台湾的年代,味蕾的鲜甜甘美,全凭着人们的口耳传播而被记忆下来。而随着经济发展,台北食肆与食事,都越见精致,昔时所谓美食美点,往往是相对于艰困的岁月、以及那一颗颗容易满足的味蕾而来的。这样的味蕾记忆,无法在连锁餐厅里找到,也无法与我们的子姪辈交换,那是属于筚路蓝缕年代的共同记忆!
尽管,共同的记忆里,还是有着不同的酸甜苦辣。
本文取自《台北旧事──一个外省第二代的生活记忆》专书
本专栏与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合作
梅花新闻网原始网址:【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-2】味蕾记忆里不同的酸甜苦辣
原始新闻来源 【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-2】味蕾记忆里不同的酸甜苦辣 台湾邮报.